大数据商业化让个人隐私无处遁形
在互联网时代,虽然网民可以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藏于各种网名之后,你如果没引众怒,也就罢了,但是若不小心在这原本平静的池塘里搅了一下,瞬间会引来多人的围观,甚至你将在短短时间内被网民揭开层层面具,然后将你毫无保留地挂于网络世界最显眼的城门口示众。
在中国有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来形容这一行为——人肉搜索。
当一个人被“人肉搜索”之后,比扒光衣服站在舞台上跳艳舞还恐怖。
这还只是互联网时代,基于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发生的动作进行总结。而进入可穿戴设备时代,不仅仅是我们生理、心理的体态特殊数据化,作为连接人与物的智能钥匙,将会让一切的人与物的特征都数据化。
我们似乎将生活在一个透明的时代,一个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时代。在法律法规与道德都缺失的年代,我们如何让自己活得有一丝隐私的空间?
“被遗忘权”真的能被遗忘吗?
尽管我们似乎对这方面的隐私不报太高的期望,或者寄希望于“倒霉”不要临到自己,但我们还是拥有这样的权利。
欧盟最高法院于2014年5月裁定,允许用户从搜索引擎结果页面中删除自己的名字或者相关历史事件,即所谓“被遗忘的权利”。根据该裁决,用户可以要求搜索引擎在搜索结果当中隐藏特定条目。
2014年6月26日,谷歌宣布,已经开始根据欧盟最高法院的裁定,在搜索结果中删除一些特定内容,给予用户“被遗忘权”。
谷歌表示:任何个人提交的请求必须指定他们希望删除的链接,以及删除的理由,这些理由必须让谷歌内部审查小组满意。
对于那些通过审核的请求,谷歌将在28个欧盟成员国的谷歌网站搜索结果中删除相关链接。
而有外媒指出这种“被遗忘权”根本无法完全兑现。
这或许就是数据化最真实的写照,只要硬盘还存在,数据依然存在,只是在某一个层面消失而已。
而云服务的开启,或许我们未来的数据存储不一定是在特定的服务器上,或许印度专门提供了计算、分析心率的云平台,非洲提供了计算血压的云平台,美国提供了分析微表情的云平台。
我们的数据将被打散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要想彻底让数据消失,或者说从地球的上抹去一个人的痕迹似乎越来越不太可能了。
而就国内的法律来看,目前我们更是缺乏关于个人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大数据时代下的隐私保护法规。相关的界定至今也还未成形,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奢求过这种权利。
大数据商业化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通过各种联网的移动设备,结合各大搜索引擎中留下了自己零零碎碎的痕迹,以及在各种场所消费所留下的记录,再借助于不断发展的数据计算分析,那些有意于利用这些数据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借助于这些零碎的数据信息拼凑出一个现代意义上完整的人。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是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了威胁,而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无疑加深了这种威胁。
大数据时代,数据被奉为一切服务的起点与终点。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360度无死角监控的环境里,周边仿佛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你,以全景式方式洞察着你,同时又有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将你完全淹没其中。
对于置身其中的用户而言,一方面渴望大数据时代,给自己带来更为贴心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忧着自己的隐私安全遭受侵犯。
这种焦虑从近期谷歌眼镜在发布过程中屡屡受挫就能体现,即使谷歌眼镜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还是无法阻挡人们对数据安全的担忧。
曾经看到一则带点滑稽的新闻,即谷歌能够通过扫描你的邮件,获知你接下去要做什么,如果它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你有自杀倾向,会贴心地为你推荐几类用于自杀的药物或者方式,保准让你死得妥妥的。
于大数据时代而言,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商家与商家之间,用户与商家之间的隐私之战。对于商家来说,谁更靠近用户的隐私,谁就占据了更多的机会;于用户而言,保护隐私,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
可穿戴设备时代的隐私权
可穿戴设备时代的来临,将完全激化这场个人隐私与大数据商业化之间的矛盾,因为可穿戴设备的核心是个人数据价值的挖掘与利用,而同时用户也越发开始重视自身的隐私安全,并且正在努力寻求途径维护这种权利。
可穿戴设备时代同时也是真正的大数据时代,此外,可穿戴设备时代将为大数据的商业化提供持续深耕的最佳环境。
整个可穿戴设备时代生态圈的建立,是基于平台的搭建和协同,而背后真正支撑这一切得以运行的是数据的获取、分析与结果反馈。
如何在可穿戴设备时代,于大数据商业化与用户隐私保护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是这整个时代都无法绕过的一大问题。
欧盟的“被遗忘的权利”基于删除某些用户认为侵犯到个人隐私的信息之上,我认为这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目前有报道称,谷歌已经陷入了“两头为难”的境地,即用户要求删除含有自己姓名的信息,而后各大媒体联名表示反对,认为这导致了他们的许多报道不知所踪。
关于大数据商业化与用户隐私保护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欧盟迈出的这第一步,或许会收效甚微,但至少已经在提示所有人,大数据的商业化是大势所趋,而个人隐私保护也正在随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响应,未来,将在法律层面赋予每个人去捍卫自身隐私得到保护的权利。
美国也在近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试图管理用户的数据隐私,这对于用户的保护意义显然是存在的,但还是难以平衡商业与隐私这一对矛盾。
不论这对矛盾如何演变,有三方面是肯定的。
一是一切都将数据化的时代是必然趋势;二是人们对隐私的权利意识将越来越强烈;三是各国对于数据安全的意识与监管越来越完善。
或许未来,我们将会在数据隐私与商业化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契合点。
谷歌眼镜为啥消失了
1897年,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布劳恩设计出世界上第一部阴极射线管,并且以其为基础制造了示波器,让人们能直接看到电流的变化。
三十年后,采用了相同原理的第一台电视诞生;从那时开始,屏幕就变成了一扇任意门,带我们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
人们总是在追求色彩更亮丽、更轻薄和更节省能源的显示方式,而阴极射线管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
于是在走过了七十年的光辉历程后,阴极射线管屏幕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家用和商业市场上让位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明的液晶屏和等离子屏。
新出现的屏幕们往往是一个个小格子紧密排列而成,最终如马赛克般拼出画面:等离子屏幕其实是诸多小型日光灯,而液晶屏则是装满了液体的大量小胶囊。
这些技术现在已经成熟,但是人们的需求永无止境。
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的发展革新,为屏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者,它们可能会让屏幕的概念变得模糊起来:采用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的屏幕可以弯折或者透明;以EInk为代表的电子纸屏幕正在压缩传统书籍的生存空间;量子点屏幕可能会在几年之内成为家用显示装置的标配;眼镜甚至隐性眼镜式显示器让显示无所不在——甚至还有直接刺激视觉神经以产生光感的设想,能彻底让屏幕遁于无形。
OLED也许可以算得上是屏幕界的明日之星。
它的每一个显示单元都像个汉堡包,顶层和底层是电极,中间夹着薄薄一层发光材料。
当通电时,电子从高能级迁跃至低能级所释放的能量将会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出来——和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发光二极管是同样的原理。
因为使用材质的不同,OLED产生出红、绿和蓝的显示器三原色,组合成各种不同色彩。
这种技术虽然1975年就已经被发明,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显露出巨大优势而成为厂商们追逐的热点:它不需要背光源、电压低而发光效率高,对比度和亮度都相当出色,而且更轻更薄、响应速度比液晶屏幕快得多。
除了这些在显示性能上的优势之外,它还有其它额外奉送的优点:采用不同的基板材料和不同的电极,人们已经可以制造出能够卷成一卷的柔性显示器——虽然还不能像纸张一样对折压扁,但是已经可以缠绕在几毫米直径的管子上——和透明显示装置,让“屏幕”的概念一再被颠覆。
当柔性屏幕和透明屏幕不只是科幻和奇幻电影中的道具时,我们的生活也会如同注入了魔法般。
窗户和镜子可以显示画面、信息甚至作为照明灯具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尺寸可以变得更小。
屏幕可以跟随着墙壁的走向而弯折,可以幻化出任何能想象得到的景致。
海报可以针对每一位观众的兴趣而显示出不同的内容,GPS和仪表盘可以直接呈现在汽车风挡玻璃上——这些都不再是幻想。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能买到使用OLED作为屏幕的手机,更多的OLED产品也在研发中。
东芝已经开发出拥有透明屏幕的笔记本电脑,能够达到60%的透明度;至于可以卷成一卷的屏幕,更是从七八年前就出现在科技产品展上了。
这些产品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在市场上,是因为成本和良品率的限制。
对OLED产品的封装还是技术难点之一,而在柔性屏幕的加工过程中,多层电子元件之间微小的错位都会产出废品。
这些技术问题可能会在几年内获得突破,但是在那之前,大块的柔性或者透明OLED屏幕依然只能在实验室和试制车间中见到。
在OLED屏幕努力踏入商业化时代的同时,更多的竞争者正在虎视眈眈。
我们在Kindle或者其他电子书上看到的Eink电子纸技术虽然极其省电,但是它的刷新率实在太低而且不能显示真正的彩色,因此只能用于极其有限的用途;但是一种新的屏幕似乎有取代OLED的可能:量子点屏幕,在具有OLED所有优势的同时,还能绽放出更艳丽的色彩。
“量子点”这个听来有些科幻的名字是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学家提出的,也往往被叫做“纳米点”或者“零维材料”。
量子点是一类特殊的纳米材料,往往是由砷化镓、硒化镉等半导体材料为核,外面包裹着另一种半导体材料而形成的微小颗粒。
每个量子点颗粒的尺寸只有几纳米到数十纳米,包含了几十到数百万个原子。
因为其体积的微小,让内部电子在各方向上的运动都受到局限,所以量子限域效应特别显著,也让它能发出特定颜色的荧光。
在受到外界光源的照射后,量子点中的电子吸收了光子的能量,从稳定的低能级跃迁到不稳定的高能级,而在恢复稳定时,将会将能量以特定波长光子的方式放出。
这种激发荧光的方式与其他半导体分子相似;而不同的是,量子点的荧光颜色,与其大小紧密相关,只需要调节量子点的大小,就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纯色光。
和OLED类似,量子点屏的每种颜色的像素都和一个薄膜发光二级管对应,由二极管发光为量子点提供能量,激发量子点发出不同强度、不同颜色的光线,在人眼中组合成一幅图像。
由于量子点发光波长范围极窄,颜色非常纯粹,所以量子点屏幕的画面比其他屏幕都要更清新明亮。
韩国的三星电子在今年二月份发布了全球第一款4英寸全彩色量子点显示屏,颜色和亮度更高,但是成本却只有OLED屏幕的一半。
当这种技术变得更加成熟的时候,也许有实力和OLED一决高下呢。
如果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块屏幕也许就可以满足人们所有的需求,只要这块屏幕放在合适的位置——比方说,人们的鼻梁上。
从去年谷歌宣布开发眼镜式显示器开始,各大IT厂商们似乎一起发现了这片新蓝海,纷纷投身其中。
到了今天,没有开发眼镜式显示装置的IT厂商反而屈指可数;因为人们都意识到,能在每天大部分时间占据人们整片视野的设备,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有了六百年历史的透明薄片。
现在已经进入测试阶段的谷歌眼镜,采用的是投影技术,即把一小幅画面直接从眼镜框上投射进使用者的眼睛,原理和家用投影仪类似。
考虑到当前的技术水平,这可能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
在谷歌眼镜开发团队中,有个人的名字十分突出:克·帕尔维兹,一位曾经供职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曾经在2008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款隐形眼镜显示器。
在当年,他已经实现了在隐形眼镜上显示图案、传递数据和无线供电的功能,但是这种和眼镜紧密接触的显示装置还需要经受更多的考验。
毕竟,当我们眼睛和世界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眼皮——也不复存在时,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带来巨大的不幸。
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想见他在谷歌眼镜团队中的作用;也许再过三五年,屏幕将会直接贴在我们的角膜上,把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叠加在一起。
在那时,屏幕就会成为非常个人化的工具,现在这种满世界都是的屏幕甚至也许会渐渐消失;毕竟,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占满整个视野的显示装置,又何必在其他地方多摆几块呢。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屏幕这一连接我们和数字世界的工具将可以完全消失——更精确地说,成为我们身体内植入的一个小器件。
人们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发现,直接以电流刺激视神经来产生光感,以这种方式来再造视觉也水到渠成;就象我们已经可以以人工耳蜗的方式让听觉障碍者重获听觉一样。
之所以能够把屏幕植入脑中,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其实与数码相机有些相似之处。
眼睛的角膜和晶状体相当于镜头,眼球后方的视网膜是感光器件,视神经等同于连接感光器件和存储卡之间的线路,而大脑后部的视觉皮层则是存储卡和后期处理软件。
使用电流刺激视觉神经,就可以让大脑接收到视觉信号——虽然实际的过程相当复杂。
在这个领域,人们已经尝试了近40年,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帮助特定眼部疾病患者获得光感的人工植入设备,但还远远无法与演化了上亿年的视网膜相比。
也许在本世纪之内,我们才会看到真正与原生视网膜效果一样的体内植入屏幕,甚至会让大脑无法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才是虚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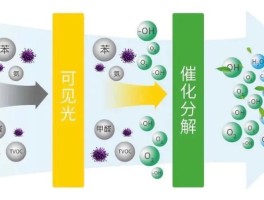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