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满的现实,人们会发现:现实的势力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改变现实意味着与现实对抗,抗争中需要坚定信念,要百折不挠,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当初记者柴静因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搅动了舆论场。它从公众健康的视角道出了雾霾的真相和根源,以及相关部门不作为的治理过程。
柴静唤起了公众对环境的关注。
这部片子很快被全网禁播,柴静也因此基本被媒体封杀。
因为纪录片揭露的内容,在改变大众对环境污染的认知程度,在改变真相永远被掩盖的媒体环境。
相比较不敢报道,或者隔靴搔痒式的报道,这种改变需要极大的勇气。
从有这个想法的开始,到自费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到纪录片的播出,我们难以想象她所承受的压力和恐惧以及痛苦。
这就是她改变现实的那份独特的勇气。
再看报道了鸿茅药酒的谭秦东、揭露火疗真相的公众号,他们无一不是在改变现状,无一不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改变现状,而这些改变无疑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有多少人对雾霾天已经习以为常,人们见到蓝天会发出惊呼,觉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难道生活在一片蓝天下不应该是人们的正常生活状态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已经被内化了,已经接受环境在毒害我们现实了。没关系大家都没事,我也不会有事的,得癌症的毕竟是少数、同样的,鸿茅药酒我不买就是了,受害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家人。
当我们作为个体去改变固有的旧模式风险太大了。
改变现实比接受现实需要更大的勇气。
穹顶之下为什么遭到抨击
《穹顶之下》所提出的治霾方案立论了。
总结一下,《穹顶之下》对于中国治理雾霾主要开了三大药方:一、减煤或洗煤,多用天然气。
二、能源破垄断,还市场权力。
三、工业到生活,节能以减排。
那么这三大药方是柴静自己想出来的吗?或许是,但我不经意间发现,这三大药方跟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多年来向中国政府推销的方案不谋而合。
而每一药方柴静都貌似有意向公众隐瞒了一部分真相,我来补充完整。
药方一:减煤及洗煤,天然气替代。
NRDC研究员文章中提过:“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是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也是主要污染源。
把煤炭消费量降下来,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加强煤炭的清洁化和高效化的利用,都会很明显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来源:华沙气候谈判大会的遗产是什么。
《世界环境)洗煤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应该大力在烧煤企业推广。
其实减煤及洗煤这一方案也并不是新药方,中国已经开始执行。
2013年环保工作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明确表示,北京、天津和河北将削减煤炭6300万吨。
(来源:治理雾霾需限煤与清洁用煤并举,国土资源部官网,2014-02-18)。
谁都知道天然气比煤燃烧清洁,那么能否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呢?中国能源的现实是“富煤、缺油、少气”,依靠国内开采来用天然气大规模替代煤并不现实。
因此中国政府2014年跟俄罗斯签订了长期的天然气采购合同,当时还遭到了如今热捧柴静公知和媒体的大肆抨击。
然而,柴静把中国天然气使用少的原因归结为“垄断,缺乏竞争”,这种说法论证不足,主要还是中国的天然气探明储量有限。
东南亚多数国家四分之三电力来自煤电,使用天然气比例更低,也是因为国土资源少气所致。
药方二:能源破垄断,还市场权力。
NRDC在中国的工作便有一项专注于市场转型领域。
《穹顶之下》为了继续论证中国雾霾是因为能源领域垄断造成天然气开采不足,拿美国举例“拿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
”这更加荒谬。
首先,双重标准,美国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是包括了大石油集团下属的区域分公司,甚至有的是单个油井一个公司,而中国也用同样标准计算的话,石油天然气起码也有几百家公司。
其次,根据著名民调机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美国人最痛恨的十大行业中,垄断经营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排名最痛恨行业第一名。
[来源:盘点美国人最痛恨行业:石油第一联邦政府第二;中国新闻网,2013年09月03日]为什么柴静团队不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呢?难道打破国有垄断,还市场权力,就是为了形成更加遭人痛恨的私有垄断石油天然气行业吗?
我认同石油天然气行业应该深化改革,开放分销和部分开采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加大竞争,促进石油行业国企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
但要提防境内外资本权贵以环保议题道德制高点切入裹挟民意以开放市场借口贱卖国有资产,搞第二波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
国有资产是全民财富,侵吞国资是最大的贪污腐败。
虽然。
药方三:工业到生活,节能以减排。
节能减排(碳)是NRDC在中国推进的最关键内容。
而这才触及环保议题的核心——碳交易,而碳交易的本质是国际政治博弈。
碳交易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工业、生活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形成温室效应,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而这会带来许多灾难性的问题,如北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
因此世界各国要通过节能减排二氧化碳来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恶化。
这个故事很美很纯洁,但是这只是表层而非真相。
真相是英法德等欧洲老牌发达工业国,由于人口规模不够以及产业转移,本国的工业经济处于停滞甚至退化的阶段,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政治话语权逐步萎缩。
但欧洲并不甘心,它自己衰退了,也想限制其他工业国的发展步伐,并重回国际权力中心,因此高举环保这杆道德大旗,推动全球34个主要工业国在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把节能减排倡议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
但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以《京都议定书》“会破坏美国经济竞争力,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名宣布退出,至今也未签署,说明美国看破了节能减排承诺是欧洲设下的圈套,不希望本国工业发展受到限制。
主要工业国中也就只有美国没有签署,欧洲和中俄日都已签署。
碳交易说白了就是每个国家制定2020年相对2005年的减排目标,达不到就交钱买别国的碳余额。
一般来讲,发达国家1吨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是100美元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成本才20美元左右。
貌似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有利,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由于话语权小往往要承诺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减排百分比目标。
例如,欧盟承诺到2020年要比1990下降20%。
美国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17%的目标。
而日本原来承诺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减排25%,但因为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在2014年2月华沙气候谈判大会上提出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反而还增加3.8%的排放。
而与此同时,NRDC竟然提议中国把2020年的减排目标提到上限,就是比2005年减排45%。
这么明摆着欺负人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怎肯乖乖就范?但一年后的同一天(2015年2月28日),柴静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就席卷全国了,人人热议,环保似乎瞬间成了头等大事,“私人恩怨”裹挟汹涌的民意施压,欧洲用坚船利炮逼不下来的中国承诺减排上限,恐怕就被这一部记录片轻松搞掂。
恰巧,今年要签署新的气候条约。
NRDC中国项目主任在2013年2月发了篇文章《中国急需一场减少和防治污染的全民环保战》,“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中国项目自2005年以来就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保。
七十多年前毛主席领导过一场人民战争,现在我们急需另一场人民战争,一场减少和防治污染的全民环保战。
”看起来倒像是今日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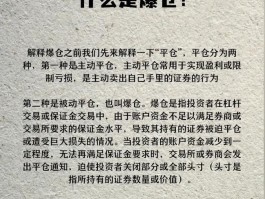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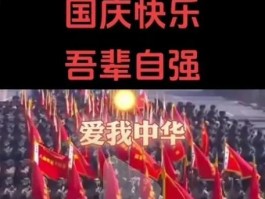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